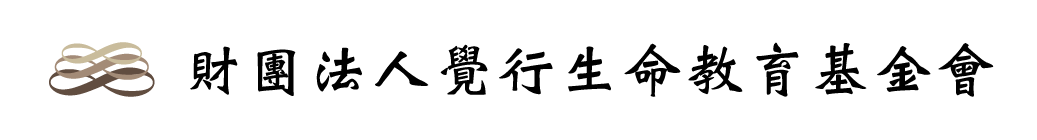「十字真言」的拜懺(真誠信實愛和恕禮善同),其實重點在於「認錯悔改」,還有「迴向功德」。
文|李昭賢(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博士)
如果說人生有70年,至今我已快過了一半。之前許多年,是段漫長又灰暗的歲月。若用球賽來比喻,是落後好幾分的上半場。從現在回想過去,大概可以粗略分成三個時期:小時候、大學時,以及認識朱慧慈老師之後。
初識我「佛」,萌發「我」識
大約是在我讀幼稚園與小學三年級之前左右,我有幸偶爾會參加學佛營,那是我最初開始知道有佛的時候。記得大雄寶殿的佛像,是我記憶中最大、最廣的雕像和建築物,小時候總以為那是要花一整天才走得完的大廣場。
也是在那樣的場合,曾有位埔里地藏院的出家師父教導我,常念菩薩聖號,於是這樣的念頭,深植到小小年紀的我的心中。我真的很聽話地開始無時無刻就小小聲念「南無地藏王菩薩」。只要沒有在上課、寫作業,我都會小小聲念,至少可以確定的是,心裡頭是有聲音的,一個字一個字在心裡頭念出來。
這樣每天每天持續了約有兩年吧!就這樣在我小學時,有一天夜裡,竟在夢中浮現「地藏王菩薩」,全身金光。雖然在夢中沒有話語,但卻讓我渾身充滿喜悅跟舒暢感。這種感覺維持到我睡醒,那一整天都很快樂,難以言喻的開心。後來的我才明白,那大概就是所謂的法喜吧!
但這種好景不常……
小學時,我不知何故,特別喜愛看武打電影,不論是成龍、李連杰,或是更早期的李小龍、劉家良的電影,我都很愛。甚至愛到經常模仿武打明星的帥氣動作,於是我開始跑跳樓梯,甚至自己練「鯉魚打挺」的動作(平躺在地上,不用手,雙腳曲到胸,用腰力和以肩膀頭頸做為支點,原地彈起,最後雙腳著地讓身體立起)。
我完全不聽媽媽的勸導,執意在媽媽的彈簧床上練,練習總會失敗,失敗的代價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胸椎和頸椎摔歪掉,導致脊椎歪斜,姿勢不良,發育不好,渾身不適。但這已是後話了。
沒聽媽媽的話,是我「執著自己可以,自以為是」的開始,認為媽媽只是窮緊張,甚至覺得如果都聽媽媽的,那不就什麼都不用做、什麼都練不成了嘛?
這份「我執」在我心中作用著,記得當我這樣想的時候,我也就越來越少念菩薩聖號了。
自高貢慢,漸釀成禍
在台灣,傳統社會裡,多數家庭或多或少都會幫他們的小孩算命。我媽曾說,在我剛出生沒多久,有排過命盤,上面告誡著我不能去「陰廟」和「墓地」,還有不能「吃牛肉」。可這些對高中大學年紀的年輕人而言,毫無根據的禁忌,聽過就像耳邊風一樣,完全不相信,也不太想理會。
叛逆期的我,也是這麼認為的。
剛進大學時,我因為擔任班代,又選上系學會副會長,有些意氣風發。於是自以為是的傲氣,也逐漸在心中升起。所以,在選課時,我也總喜歡選一些別人覺得很硬,避之惟恐不及的課。有一門客家文化的通識課,就是典型的例子,該課的授課老師,是出了名的嚴格,他要求每位學生都要在學期末,去客家庄做田野調查,才能寫期末報告,而且不可以抄襲網路上或是專書上的資料。
於是,我為了客家文化課程的報告,前往新竹客家庄訪談。
當時是住在一位當地客家人的學長家裡,我就以訪談他的奶奶為主,因為他奶奶只會說客家話,過程中就由V翻譯。其它的景點,也由學長開車帶我去走走看看,拍拍照留影。
新竹客家庄最著名的景點,無非就是北埔、義民廟,還有都城隍廟。我最先到北埔的老街,看到了客家傳統老房子,目睹了牆上曾經戰火的痕跡。
之後到褒忠義民廟。那是我人生轉折點的地方……
在廟門口,我想起我不能去陰廟的忌諱,但又很想不相信。於是我打了通電話給媽媽,跟她說我來到了義民廟,我要進去了。電話那頭,媽媽不斷勸阻我,我卻以「別人都可以,為什麼我不行」來頂嘴。掛斷電話,我便帶著「我慢」的忿忿心情,大步走進廟裡,在跨過廟門時的瞬間,感到有種透明的電網,從我腳下通過全身。
不以為意的我,繼續我行我素,記得也沒有燒香,也沒有稟明我的來意。甚至跟著學長前往後殿的塚,還在那拍照。相當的沒禮貌。
冒犯了義民廟。回來之後,便開始嚴重的大吐下瀉,甚至幾近瀕死狀態,跑遍中部各大醫院診所,無論如何就是找不出確切的病因。好不容易稍有恢復,就又陷入下一個病痛折磨。有的醫生說是中暑逼到;另外有的醫生說是氣胸;西醫則說是心臟可能要進一步檢查;還有醫生說是脊椎不正所致。在醫治的過程中,始終沒多少起色,於是我媽不得不求助於「民間道教」的宮廟。
最早我有印象的是在南投工業區的慈善宮。我媽心急如焚的前往請求參天玉勒王爺救我之命。當時廟裡的師姑說我很嚴重,於是先帶我到台中找一位把脈很神的中醫師。那晚,中醫師說我經脈全亂,商請助手幫我簡單整脊和拔罐後,當場要我喝下他沖泡好的藥粉水。他要我之後再去給他看,便讓我們帶了三天的煎藥回家服用。
之後回來,一開始慈善宮的師姑說是我家有祖先的問題需要處理。但我媽告訴她,我是去了新竹義民廟之後才變這樣的,師姑頓了一頓後,似乎感應到了什麼,馬上說要我媽跟她去一趟新竹義民廟,要去幫我叫魂回來。說是有魂魄被困在那兒,王爺要前往討魂。
為此我對父母深感抱歉。因為我的鐵齒和不禮貌的行為,卻要父母為我擔心操勞。我覺得很是不孝。我暗暗在心中說,如果我能活下來,我願意深刻懺悔。
在我媽和師姑驅車前往新竹義民廟的途中,當時在家的我,狀態是最接近斷氣的時候。在房間陪我的姐姐和弟弟,說親眼看到我渾身氣色呈現暗沉,毫無血色。姐姐還因此一度泣不成聲。就在我媽和師姑到新竹廟宇交涉後不久,原本已經失去意識的我,竟開始回了神,眼睛能微微張開,但仍一句話也沒力氣說。
那時候的我,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。更不明白,為何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。明明當時只是去新竹田調,還有學長和同學陪同,為什麼他們沒事,我卻有事。又為什麼中西醫的醫生和檢查,都毫無所獲。他們最常說的就是說我是壓力太大,卻又無法解釋坐在他們面前的我何以氣色不佳、痛苦不已。
後來,我家在師姑的協助下,開始處理我家祖先牌位和神明桌的問題。也開始了我除了看醫生吃藥之外,兼跑各大宮廟、算命、收驚、卜卦的日子。
這樣的過程前前後後約有13年之久。
這中間,大約在我剛復活過來一年後,在我大三的時候,家人帶我到埔里人乘寺地藏院。突然有位出家師父表明在等我,他連問我三次「你以後要做什麼」,我回答「當外交官」,他搖頭,要我回去再仔細想想,還要我每天讀《金剛經》。他說我不可以只讀佛經,也不可以只讀書不讀佛經。要我一天讀書,也讀一遍佛經,剛開始我有聽從,但總是恆心不足,維持個一兩個月後就會中斷個幾天再接著念。
如此斷斷續續的讀經。甚至,有好幾次都會抱怨地不想念佛經,覺得念佛經沒有用,我還是過得很痛苦,還是經常地不舒服。
就這樣13年。
我一度以為自己有精神問題,好幾次去看了精神科,也去學校的諮商中心看心理醫師。但都無法解決我的痛苦。有段時間我甚至嚴重到無法出門,在學校搭電梯居然有了「幽閉恐懼感」,心跳恐懼到無法呼吸,經常想吐。而且,更可怕地是,每次到醫院檢查,結果都是正常。如此更讓人摸不著頭緒,到底是什麼原因會經常胃不舒服,頭暈想吐。實在不明白。
這樣的情況,著實嚴重影響我的學業,許多考試沒法準備,許多朋友聚餐沒辦法去,許多研討會或活動沒能參加。於是朋友越來越疏遠,越來越少,成就感越來越沒有。自信心也沒了。
那段時間,只能用「慘」和「苦」字形容。
知道朱慧慈老師,是我在念碩士班的時候。當時所上來了新的老師,姓高。他對學生很好,很容易感覺到他的善良和關心。我們學生不會好奇老師的宗教信仰,只要善良,勸人為善,其實我們是很有包容力的。後來老師提起他邀請了朱慧慈老師來學校演講,鼓勵我們(有修他課的學生)去聽聽。我去聽了。
那天,記得是一個周六的晚上,在學校某處的國際會議廳。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那樣的演講,對我的來說,是生命的衝擊與震撼。雖然對信仰佛教的我而言,「因果輪迴」與「報應」的概念並不陌生,但是,那畢竟從未真正獲得證實。對我,甚至對眾多年輕人而言,那是毫無實際感的宗教概念。
就在那天,我第一次看到朱慧慈老師,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那麼震撼的演講。真的,我至今依然印象深刻。朱老師她將她診療的案例,如實地讓我們看到因果報應,特別是所謂的「靈魂」和「冤親債主」,那樣地真實在我面前上演。
打從那一天起,我便知道,我一定也是這種緣故所造成的,冤親債主找上門。但我不清楚,在我身上,前世是什麼樣的故事,又犯了什麼樣的罪。更重要的是,即便我從身心靈促健會知道「拜懺」和「十字真言」,但卻沒有真正的實行過。更精確地說,應該說是我還陷在身體經常不舒服,難過地幾乎天天跑診所、看病吃藥,和在家休養順便怨天尤人的循環裡。明明知道這樣不行,卻又難以跳脫,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
這種情況,一直延續到讀博士班。而且,在剛進博士班沒多久,陷入更加黑暗的低潮。那時,我被甩了,身體又更糟了,家裡的情況也頗不平安,很不快樂。之後一年多左右,我原本的指導老師突然離世。讓我的畢業之路,增添不少曲折。
就在我換了新的指導教授,面對很可能難以畢業的未來茫茫然時,回去找高老師吃飯聊天。高老師聽了我的情況,他並不像別人會敷衍似的給予鼓勵與安慰。他建議我,去跟朱慧慈老師掛號吧!也許會有人醫治得了我的問題。於是我打電話到促健會預約掛號。
隔了好幾個月,依稀時間單位應該有「年」,我已經不太記得了。因為預約掛號之後,到真正要我到台北看診,這中間我又更慘了。2016年上半年,眼睛嚴重發炎,我真的好怕好怕再也看不見。那時我真正的體會到盲人或眼疾的感受與痛苦。
2017年的4月中旬,我接到身心靈促健會的電話,朱老師要看我了。那種覺得可能有救的感覺,我難以用言語形容。
那一年,我原本應該要去服兵役。但是,因為嚴重的急性結膜炎,以及無法入睡的問題,讓我體重減輕,以致後來兵役體檢改判免役。因為免役在家休養,所以能夠立刻前往台北讓朱老師看診。
第一次來到朱老師的診間,我知道了我前世,以及犯下什麼樣的錯。「太平天國」四個字原本只存在在歷史課本裡,那一刻卻離我這麼近。我有些遺忘了那段歷史,於是我上網查了維基百科,也在圖書館找了幾本書。細讀之後,我流下了說不上是什麼感覺的淚水。
真心懺悔,頭磕到落淚
這一刻,我知道我要悔改什麼,改什麼過。
我聽從朱老師的功課,每天都拜懺,向佛祖磕頭,向冤親債主磕頭。有一次的磕頭,以真心的懺悔,那次我磕到落淚。
我告訴自己,也告訴靈界,我錯了,我不該對新竹褒忠義民爺不禮貌,我不該沒聽媽媽的話,對媽媽頂嘴;我不該沒聽媽媽的話,把自己摔傷脊椎;我不該抱著想打人、想炫耀的心念去習武;更不該什麼事都只想到自己。「獲得榮耀」、「理應健康」、「受人讚許」等這些欲求,越追求越無法滿足。
媽媽好幾次都說我「太在乎自己」。我始終沒聽懂這句話,常很不滿的回應她,認為媽不懂我的痛苦。
「十字真言」的拜懺(真誠信實愛,和恕禮善同),其實重點在於「認錯悔改」,還有「迴向功德」。這個跟讀佛經的原理一樣,只是我以前念金剛經都沒有好好的懺悔和迴向。所以過去念佛經才會總覺得沒有用。因為,連「有沒有用」的念頭,都不該有。凡事如果想著「結果」才去做,就是偽善。
在朱老師治療後的變化
其實,在接受朱老師治療之前,因為曾經連絡過身心靈促健會,也收到過教學講義,我就已經知道「十字真言」的拜懺方式。但是,一直對跪拜是否有效,半信半疑。最初只是覺得,這跟我小時候去佛寺朝山一樣,差別只是朝山有在前進,而拜懺是在原地跪著拜好幾拜。
因為有疑心,所以做得不認真,也不確實。甚至覺得可能是自己操作的方式哪裡有錯,才一直都沒效。我還是一樣,經常病苦,總是會有「沖犯」到的現象,還是得去給人收驚卜卦。
後來,第一次接受朱老師治療時,才明白這都是自己的冤親債主阻礙拜懺,或是讓我無法靜心的緣故。也因為如此,我才容易有沖犯的現象,或是容易有背後起雞皮疙瘩,背脊發冷的感覺。
經過朱老師治療後,回家開始發憤認真拜懺。一開始,根本拜不完108拜。大概到了50拜,就開始滿頭大汗,腰痠背痛了。必須抱著真誠向冤親債主道歉,以及小聲念對不起的決心,才能堅持拜完一輪108拜。
這樣持續拜懺了一兩天後,就可以一次拜到三輪,甚至四輪。而且,真的如朱老師所說,當我用最真誠的心去拜的時候,效果最明顯。坦白說,大多數在拜懺的時候,很容易有雜念,或是好像在趕東西似的,或是像每天的例行公事似的,有點敷衍的在拜。那種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還是會再來,還是幾乎天天在看醫生。在給朱老師治療之前,曾因為太常看醫生吃藥了,被健保局的來函警告。那樣的日子,藥罐子的生活,真有種生不如死的感覺。
我是2017年的4月中旬,第一次接受朱老師的靈療。大約到了6月左右,等於是拜懺了約有2個月,我的氣色就漸漸紅潤起來,比較沒那麼暗沉無光。雖然身體還是很瘦小,體重還是很輕,但說實在的,整體的體力的確變得比較有元氣。更重要的是,不,應該說是很神奇的是,有天晚上,做了一個畫面很清晰的夢。
說到夢,先說我曾跟朱老師提過,從小到現在,我曾有做過兩次一模一樣的夢境。這中間相差至少十幾年以上,但卻做著同樣畫面的夢境。在夢中,我跟著一大群人奔跑著,整個背景是火紅色的,每個逃跑的人都很驚慌。因為背景顏色太過火紅,紅紅亮亮的,使得每個人都呈現黑衣人似的顏色。而這樣的夢,是相當清晰,令人印象深刻的。
朱老師說,那是我前世歷經戰火的記憶。
因此,我對於拜懺2個月後,夢到畫面相當清晰的夢,特別留心。或許是因為我經常向神明或佛祖問「為什麼我會這樣子」之類的問題。所以,在那次的夢中,我確實聽到有個宏亮的聲音,對我說祂要帶我去看一些事、一些畫面。
很快地,宛如變魔術一般,我像是旁觀者在看電影,在天空中飛翔地向下看,看見一群穿著清朝服裝的人。夢中的場景,那是11月份的夜晚,不確定是哪個古城,跟拍古裝片的房子很像。當時的天氣已有些寒冷,有幾位穿著清朝服飾的人,暗地討論著,並且真的按照計畫舉事,在一場深夜的戰役中,把一群貪官汙吏通通一網打盡,抓起來痛打。看起來,那個領頭的人是個文武雙全的人,既有頭腦謀畫設計陷阱,又有武功的對人拳打腳踢。
看著像是幻燈片,又像在看電影的畫面,突然那個宏亮的聲音對我說,「你看到了吧!冤冤相報何時了。」我在夢中,對空中那宏亮的聲音問道,「但明明就是那些貪官污吏的錯,用公權力奪取百姓的血汗錢,傷害百姓,還開賭場和妓院,難道不該有人教訓他們,將他們繩之以法嗎?正義何在?」那宏亮的聲音告訴我,「什麼是正義呢?把他們抓起來痛打一頓,甚至打死了,就是伸張正義了嗎?」
我沒有答案。隨後我醒來。一臉茫然地躺在床上,兩眼直視天花板一段時間。我不知道有多久,但我覺得好像這夢境是在告訴我,何以我會過著體弱多病的原因。但我不確定。
等到再去朱老師那治療時,我把這夢告訴朱老師。
朱老師告訴我,那是前世在太平天國對清朝發動起義的戰亂畫面。
我覺得很可怕,因為我從小自有記憶以來,就對武術特別喜愛。但是每次練習武術,或是去找老師學習拳法,不論是少林拳,或是太極拳也好,總是剛開始好像越來越健康,到了學完一套完整拳法,就開始渾身不舒服,痛苦不已而無法再練。讓我媽認為,別人是越運動越健康,我卻越練武越不舒服。或許就是前世因果的緣故。
朱老師說真正的原因,在於我習武的念頭不對。不論是前世或現在。我覺得很震撼,因為我真的每次學習武術的時候,內心總有個念頭,認為拳法就是用來格鬥的。能打能用的,才是武術。而我之所以自小就對武術有興趣,甚至一看就會,居然是因為前世的因素。每個人的天賦,與生俱來的特殊能力,原來並非真的天才,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輪迴轉世,因為上輩子的所學,這輩子才會覺得異常得心應手。
後來,我向佛祖發願,我不再習武練拳,我要改掉想學格鬥的念頭。
於是,平常一樣拜懺與迴向冤親債主,大約到了2017年的7、8月之後,那種經常沖犯到,或不舒服,或不自覺地不敢出門搭車的現象,就越來越減輕,減輕到9月份開始,我有一次可以獨自去台北面試應徵工作。雖然還是會有些想反胃的不適感,或緊張感。但是,至少還在可以忍耐的範圍。這對我來說,真的是一大進步與改變。因為長年來,我每次出遠門,都一定要有家人陪伴,不然很怕會不舒服到無法自行回家。念碩士班時,曾有次到台北,突然頭異常的暈,便坐倒在台北車站的地上多時。那是很可怕的回憶。
2018年初,還可以準備國家考試,並且自己前往考場。肚子不適的感覺,以及緊張焦慮不安的感覺,雖然減輕許多,但多少還是有些負面想法會出現。我就會默念「真誠信實愛,和恕禮善同」或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來轉移注意力。坦白說,我不會去誇口說這樣默念有什麼多大的效果,但至少我要相信,會越來越好,因為我願意懺悔自己過去所造的過錯。
經過幾個月,朱老師的診療與開示點化,我知道我錯在哪了。
多年來,我太過執著於「應該如何」,認為誰誰誰應該如何,沒有就是不對。那種「非白即黑」的念頭,導致我內心糾結,自己綁死自己。我想,之前那個清晰的清朝夢境,應該看到就是我前世就存在過份的正義感,過度非白即黑的習氣。總覺得很多事情,很多人應該要怎樣,沒有怎樣就是不對的。而我自己就是在導正那個不正確,或是伸張那個正義。
此外,太過執著、追求「我自己的」、或是自己嚇自己的種種想法,都是妄念。就連「沒有成就感」、「沒有信心」、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」、「我會不會怎樣」、「我也不想要這樣悶在家裡」等等的念頭,都是自私自利的想法,都是充滿「自我」和「我慢」的想法。
多年來,我忘了單純念佛和讀書的活在當下感。只知道想「獲得」(TAKE),而忘了想「給予」(GIVE)。拜懺和迴向功德,就是「施」與「受」的道理。因為過去所有因貪嗔癡犯下的罪業,都是只想「自己」、只想「貪得」而帶來的心念與反應。
直到朱老師用太極的觀念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的新解,才點醒我這些錯誤的想法。而這些想法和念頭,原來很早很早之前,媽就在勸我了。因為媽常念我,「太在乎自己」了。
我才知道,因為太在乎自己,所以高傲自大,所以自以為是,所以對靈界沒有禮貌,對父母師長也沒有禮貌。因為太在乎自己,所以沒做善事,所以讀佛經不求甚解,所以不懂低頭悔過,不知道都是自己的錯。
經過朱老師治療滿一年的此刻,我才知道,要聽媽媽的話。而且,要聽懂媽媽的話。
「行是知之終也。」朱老師如是說。知,然後實踐,經常覺察自己,知行合一,才是真正「知」道。
這一刻,我的人生下半場才要開始……